近期学习两高两部《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涉及此类刑事案件犯罪数额如何认定的具体问题进行讨论。我们遇到一起刑事案件,在犯罪数额方面同样步入这一指控思路。这一认定思路是否能扩大解释?是否存在类推解释之嫌?本文将展开探讨。
一、问题的提出
上述《意见》第6条规定:
在认定“套路贷”犯罪数额时,应当与民间借贷相区别,从整体上予以否定性评价,“虚高债务”和以“利息”“保证金”“中介费”“服务费”“违约金”等名目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非法占有的财物,均应计入犯罪数额。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际给付被害人的本金数额,不计入犯罪数额。
也就是说,在套路贷刑事案件中除本金以外的所有所得均应计入犯罪数额,即将双方经济往来相互折算,之间的差额即是犯罪数额。这一认定方式确实极为简单,旨在从严打击“套路贷”刑事犯罪行为。而我们所办理的刑事案件并非“套路贷”,仅涉及高利借贷问题,检察机关指控获取高额利息过程中存在“威胁、恐吓”行为(该案是否有威胁恐吓行为尚存疑,但并非本文讨论的焦点,本文以假定威胁恐吓行为存在为前提展开讨论),构成敲诈勒索犯罪。在犯罪数额的认定上,检察机关同样适用了“从整体上予以否定性评价”的指控思路,这一思路是否正确?是否矫枉过正或过于严苛?
二、“从整体上予以否定性评价”的前提
笔者认为,“套路贷”刑事案件犯罪数额的适用“从整体上予以否定性评价”有其特殊原因,这一适用是否及于其他类型的犯罪行为,以该犯罪行为是否匹配该“特殊原因”为前提。
“套路贷”刑事案件犯罪数额“从整体上予以否定性评价”,主要原因在于该类犯罪行为自始至终就具有“套路性”特征,从行为的初始就具有对他人财物予以非法占有之目的。正如上述《意见》前两条对“套路贷”行为界定的那样:
1.“套路贷”,是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假借民间借贷之名,诱使或迫使被害人签订“借贷”或变相“借贷”“抵押”“担保”等相关协议,通过虚增借贷金额、恶意制造违约、肆意认定违约、毁匿还款证据等方式形成虚假债权债务,并借助诉讼、仲裁、公证或者采用暴力、威胁以及其他手段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的相关违法犯罪活动的概括性称谓。
2.“套路贷”与平等主体之间基于意思自治而形成的民事借贷关系存在本质区别,民间借贷的出借人是为了到期按照协议约定的内容收回本金并获取利息,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也不会在签订、履行借贷协议过程中实施虚增借贷金额、制造虚假给付痕迹、恶意制造违约、肆意认定违约、毁匿还款证据等行为。司法实践中,应当注意非法讨债引发的案件与“套路贷”案件的区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也未使用“套路”与借款人形成虚假债权债务,不应视为“套路贷”。因使用暴力、威胁以及其他手段强行索债构成犯罪的,应当根据具体案件事实定罪处罚。
从上述界定可以发现,“非法占有为目的”是套路贷行为初始即具有的主观心态,该行为实施本身存在大量“虚假性”的表象,而且行为本质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并非以获取约定利息为实质目的,获取其他诸如抵押房产等不合理高额利益才是行为的核心目的。这一特征正是套路贷行为与普通民事纠纷存在的最大区别。正因为如此,将民事法律关系中合法范围内的利息也作为否定性评价的一部分,也有其合理性的考虑,毕竟刑事法律的一项基本原则是“任何人不能通过其犯罪行为获益”。但前提条件必然是,“非法占有目的”这一初始行为心态和目的必须达到刑事证明标准。
三、非套路贷案件犯罪数额认定的分析评价
回到我们所办理的案件,存在高利借贷行为是客观事实,但双方从借贷关系发生的初始对于借贷合意的形成、利息的约定等行为并没有任何“虚假性”的表象,也没有强迫借贷,后期借方难以还款导致利息逐渐攀升,纯系借方经营原因,也与贷方的任何行为没有联系,贷方所主张的利益也没有超出曾经约定的利益范围。假设贷方在进行权利主张的过程中确实存在“威胁恐吓”行为,也不能及于所获取的所有利益,如果并不存在“套路贷”刑事案件起初所具有的“醉翁之意”,所谓一开始就对所有款项均形成“非法占有目的”,显然于理不通。
笔者在与本案公诉人进行沟通过程中,其提出在扫黑除恶大背景下,高利贷行为必须予以严厉打击,因此应当予以整体否定性评价,笔者认为这一理由并不成立。主要原因在于单纯的高利贷行为并没有达到必须予以刑事打击的程度,对高利贷行为,已经在民间借贷相关司法解释的条文中框定了予以司法保护和予以否定性评价的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
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上述条文是国家明文规定所保护的范围,简而言之就是——24%以内的予以保护,24%-36%的是自然之债已支付不支持返还、未支付也不保护,36%以上的支持返还。这一规定界定“合法”部分的范围,对于合法部分以外的,以占有为目的强行索取则“非法占有目的”的主观心态就得以成立。如果将非法性上升到全部获取的利益,则有违罪刑法定和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反而为借款人后期普遍赖账等提供了并不合理的便利条件,对于金融秩序的稳定、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等也存在极为不利影响。
因此笔者认为,在不能证成客观行为存在虚假性、也不能证成主观心态存在“套路”他人情况的前提下,不能对这类敲诈勒索行为予以整体否定性评价。
四、延伸讨论的一个问题
从本案进行扩展讨论,如果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通过威胁恐吓的方式主张这一范围内的钱款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犯罪?如果单纯从利益的“非法性”角度考虑当然不构成,但周光权老师貌似有不同的观点:
主张债权行为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需要综合考虑行为在规范的范围内是否可以容忍,以及债权行使目的的正当性、权利行使方式的相当性、手段必要性、被害者的状况等情形,如果坚持财产罪保护法益的合理占有说,对权利行使行为在理论上成立敲诈勒索罪的范围就应该适度大一些。理由在于:
(1)从保护法益的角度看,敲诈勒索罪的本质是侵害他人对财物的合理占有,在主张民事赔偿或强迫他人履行债务的场合,即使行使权利的行为在债权范围内,权利人实现了债权,但索要赔偿或主张债权的行为也可能侵害他人对财物的合理占有,被害人相应地也可能出现财产损害。实务中定罪范围过小,与财产罪保护法益的合理占有说并不一致。
(2)从非法占有目的的角度看,为行使权利而索要财物的场合,行为人至多只有债权请求权(很多时候连这种权利都没有),但没有对他人财物的占有、处分权,因此,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会侵害他人的合理占有有明知,同时,其有排除权利人,并将他人的财物(通常是金钱)作为自己的所有物的非法占有目的,因此,行使权利的行为通常也能够满足本罪的主观要素。
(3)从主张权利的程序上看,主张权利的情形,大多不符合自救行为的成立条件,不能阻却违法性。在行为人原本可以通过合法的民事程序主张权利时,对其行使权利的恐吓行为如果不定罪,等于鼓励行为人用合法民事途径之外的不法手段索要他人财物,这不利于维护财产秩序,也不利于形成国民的规范意识。
(摘自周光权著:《刑法各论》(第三版),中国人民法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34~136页。)
笔者认为上述论证并不足以支持对采取非法手段索取合法利益行为作构成敲诈勒索罪的入罪评价,主要是因为敲诈勒索罪本质上仍然是侵财性犯罪,这类行为中财产的转移占有并非由合理占有到不合理占有,而是在合理占有之间进行移转。采取非法手段索取合法利益形成实质法益侵害的仍只是手段行为,予以否定评价的不应当是手段行为背后的目的。如果手段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绑架、非法拘禁、寻衅滋事等行为均可以单独予以评价,如果手段行为没有上升到犯罪的程度,而通过敲诈勒索这一目的行为予以兜底评价显然过于严厉。
关于周老师的第三点理由,对于起到负面示范作用的社会效果考量问题,笔者认为其根源还是应当从刑事法和治安管理法去综合考虑手段行为的问题,并不必然需要通过打击经济犯罪的方式予以制裁,毕竟刑事制裁永远是最后的手段。可能也正因为如此,周光权老师在最后写道“利用恐吓手段行使权利的行为在实务中确实比较复杂,是否定罪需要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仔细权衡,切实做到不枉不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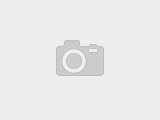 图集
图集 图集
图集 图集
图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