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听易延友教授辩护陈满案——陈满案再审旁听记

易延友教授
▍文 熊猫
▍来源 公众号辩护人
这一切最初发生在二十三年前,1992年12月25日,晚上19时30分左右,海口市上坡下村109号发生火灾,现场发现一具尸体并有打斗痕迹,死者是钟作宽。同年12月27日晚,陈满被海口警方作为犯罪嫌疑人抓获。1994年11月9日海口中院以故意杀人罪、放火罪判处陈满死缓。判决后,被告人未提出上诉,检察机关以量刑过轻为由提起抗诉,海南高院经二审裁定后维持原判。
此后,陈满及家人坚持申诉,全国诸多律师自愿帮其申诉,其中不乏刑事辩护领域中的成名大腕,但均被驳回或杳无音讯。直至2014年2月22日,陈满的申诉代理人、清华大学法学院的易延友教授向最高检提交了陈满案申诉状,案件终于出现转机:3月份,最高检通知易教授,已经指派专人办理本案;7月,最高检决定立案复查本案。2015年2月10日,最高检就陈满案向最高法提起抗诉;2月28日,最高法决定立案再审;4月份,指定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陈满案再审。
值得注意的是,本案侦查和审理阶段,多人作证案发当天他们和陈满一起吃饭,喝茶,看电视,陈满根本不存在作案时间,但这些证人证言却未能引起重视。
2015年12月29日,雨后初晴,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开庭再审陈满杀人、放火一案。海口的风咸湿温暖,扑面而来像带着眼泪的味道。笔者谨以一个庭审旁听者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聊作此陈满案旁听记。
开庭地点
一、
从形式到实质
(一)旁听提供免费水和纸笔
下午一点左右,法院门口已经高架起了摄像机,围满了大批记者和前来旁听的人。有几个称是陈满的亲友和曾经帮过陈满的律师情绪略激动,他们迢迢赶来却没有拿到旁听证,因此对法院表达了强烈质疑。
进了法庭之后,居然出现了一幕惊喜:现场发放有水,笔和一个小本子,像这样贴心的旁听待遇确实是平生第一次。相比有些地区法庭完全不让旁听人员做记录的情况,这里简直树立了文明旁听和支持旁听的典范。但想起分分钟之前的安检,又不免让人困惑。这种旁听待遇阶段反差的背后隐藏着怎样一种矛盾?
环顾法庭,旁听席有7排座位,一排坐15人,前面5排竟都坐满了。据旁边的本地人说前面的都是原办案机关人员,还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等。后面的2排坐的主要是其他旁听人员,陈满的亲友等。我旁边坐着的中年男人竟然就是陈满的同学。
庭审现场
(二)庭审讯问翻开尘封往事
审判长宣布庭审开始,首先问了陈满关于案件的基本信息,在监狱的服刑情况,接着宣读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再审决定书。
这是一场没有控方的法庭审判。和以往的“控辩双方”不同,这次法庭上用语都是“检辩双方”。陈满回答问题声音稳定,听不出什么情绪起伏,旁边他同学说:“他这个人一直就没什么脾气,关了这么多年了,你看他也没啥情绪。”
法庭调查从讯问原审被告人开始,先是陈满的第一辩护人易延友进行发问。易教授首先请求审判长能否让陈满坐着回答问题,审判长回:“你说的这些,我会适当考虑。”基于对法庭的尊重,易教授对此也未再坚持。易提的问题涉及三个方面:一是1992年12月25日案发当天,陈满从早到晚的行踪:具体大约几点的时候,见了哪些人,做了哪些事,以及案发时、案发后陈满具体在哪里,都有哪些人证实等;二是陈满被公安机关收审和讯问的过程,其所做供述的具体经过、究竟是在何种情况下做的供述等;三是陈满一审判决之后为什么没有上诉。这些问题层层推进,陈满边回忆边回答,有些细节随时间淡去,但是最为关键的他却从未忘记。
根据易教授的发问和陈满的回答,1992年12月24日晚,陈满睡在钟作宽处,25日早上9点多,他起床之后就去了宁屯大厦看工人装修;11点多的时候下楼,发现自行车钥匙不见了,他想应该是前一晚落在了钟家的沙发边儿上,就步行去找钟;大约12点到了那儿,看钟在吃午饭喝酒吃花生;钟看到陈满,问他吃饭没有,陈满回答没有,就招呼他一起吃饭,吃完陈满就走了……下午他去找夏某,陪夏某先去交了房租,接着去了公安局,出来时外面下大雨,他打出租去了滨海新村。下午5:30左右,陈满又回到宁屯大厦的702和703看工人装修;晚上6点多,像往常一样到了吃饭时间,他招呼大家吃饭;吃完之大家开始打麻将,陈满在旁边给大家倒水;7:30的时候他和大家一起看新闻联播。晚上8点,他去不夜城打了个呼机给肖波,但没有人接;晚上12点,想着是圣诞,钟又要离开海南回家,所以他去了和平南路的大排档点了三个菜还拿了一瓶酒,骑着自行车准备去给钟送行。到那边发现停电了,公安的车也在那儿亮着灯,因为担心自己工商登记的问题,加上身上没有带身份证,他要回避公安,所以就又回到不夜城看了个电影。26日早上,他和往常一样吃了早饭,去宁屯大厦看装修。
(三)冤案到底是怎样炼成的
陈满从未料想到,如此平凡的一天,竟给他带来此后长达23年的牢狱之灾。
1992年12月27日晚上,海口市公安局以收审的名义将陈满带走,开始对他进行审讯,一开始他坚持不认罪;接着他被关进小房间,被绳子捆着抽打,被铁棍打骨头关节,痛觉让他逐渐头脑空白了;1993年1月6号,在办案人员的刑讯逼供之下,陈满作出了第一份认罪供述。讲到此处,陈满的情绪激动起来,哽咽着说:“他们说这(关小房间、绳子抽、铁棍打)叫‘旅游’,说我这是‘一日游’,要是再不配合就‘三日游、五日游’,我头上伤疤现在还在!”
问及为何没有上诉?陈满说:“我不懂法律,他们(办案人员)那么厉害,已经给我判了死缓,万一我上诉他们给我加重判了死刑怎么办,我害怕加重,就不敢上诉……”作为一个普通百姓,陈满不懂“上诉不加刑”的法律原则。就算知道这个原则,司法机关打破常规加刑的事例也屡见不鲜。
陈满的第二辩护人对陈满进行了补充发问。最后检方提出了几个问题,除了之前易教授问过的为何没有上诉,主要是问陈满翻供的情况,以及当时被刑讯逼供之后,为什么没有控告办案人员?陈满说他一开始没有想到,再一个也担心说了没有用,结果会更可怕。
整个讯问的过程中,陈满一直站着说话。他个子不高,隐约能看见他的背稍微有点儿弯,头却一直昂着。审判长充分保障了辩护人发问的权利和被告人的表达权利,接着宣布发问阶段结束,审判长让陈满坐下,进入庭审质证阶段。
二、
从证据到事实
(一)重新审视原案证据
原案证据主要分为三类,一是物证,以及与物证相关联的现场勘验笔录、鉴定意见等,但是案件相关的重要物证大部分缺失;二是证人证言,但是对证言的采信存在偏颇;三是陈满的有罪供述,这是定罪的主要依据,但却是通过非法讯问的手段获取的,真实性存疑。
易延友指出:据现场勘查笔录,侦查人员在案发现场收集到大量物证,包括带血的衬衫、海南日报、破碎的酒瓶、散落在现场的刀具等;这些物证既没有进行指纹鉴定、血迹鉴定,而且在审判前就均已丢失,从未在法庭审判中出示或辨认,缺乏与陈满案件核心事实的关联性。简言之,就是这些证据是否真实存在?是否和陈满有关?这都存在疑问,所以根本不能拿来作为证明陈满杀人放火的证据。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本案杀人工具的菜刀在关联性上存在重大瑕疵。易延友介绍,公安勘查时发现现场有五把刀;陈满先交待用过两把刀;一审判决书认定杀人凶器是“带把菜刀”。首先,如果要证明陈满持菜刀行凶,那么有两点必须证明:一是陈满使用过这把刀,刀上应该留有陈满的指纹;二是陈满用这把刀杀害钟作宽,刀上应该有钟的血迹。问题是,本案没有对刀上可能存在的指纹做过任何鉴定,根本无法证明陈满用了这把刀,杀了钟作宽。
这里涉及证据制度的基本原理,易延友解释说:所有物证与案件的关联性都是附条件的。杀人用的工具、现场的血迹、指纹、鞋印、酒瓶、血衣等物证,大都需要辨认或鉴定,才能确定与案件是否有关联性。例如,现场提取的指纹,如果没有经过鉴定,那到底是谁的指纹?这个指纹就既不能证明被告人实施了犯罪,也不能证明被告人没有实施犯罪,它与案件就没有关联性。再如,杀人用的菜刀,如果没有经被告人辨认,那这菜刀是杀人用的那把菜刀吗?如果不能确定这点,那么这菜刀就是一把普通菜刀,和案件核心事实毫无关系,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检方也认为原案的物证存在诸多不规范之处,针对所谓案发现场发现的陈满“工作证”提出了疑问,到底在哪发现的,是在钟作款的裤子口袋还是上衣口袋?是什么样子?这些都不知道,到底有没有这个工作证甚至都存在疑问。
(二)合议庭新调取的五组新证据
浙江省高院和浙江省检察院在本次开庭出示了五组至关重要的新证据:有对陈满的讯问笔录,对相关证人的证言询问笔录,海口市美兰监狱针对陈满减刑的裁定,省检察院出具的技术性证据审查意见书。
法庭质证阶段,易延友指出,这些证据一方面说明了原案对相关证言的采信存在偏颇,另一方面更加明确的证明了陈满是无辜的:首先,陈满无作案动机,证人证言说他和钟作宽的关系很好,比其他人更密切,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怀恨在心”;其次,陈满无作案时间,大量证人证言说明陈满在案发时有不在场的证据,客观说明陈满不可能是凶手;再次,案发后陈满无异常行为,他照常去上班,言谈举止也无异样;最后,陈满不具有杀人凶犯的性格,他是一个性格内敛,比较温和老实的人。
(三)史上最和谐的法庭辩论
这是一场无比和谐的法庭辩论,检辩双方基本是一直在轮流证明陈满无罪。
合议庭耐心地主持着庭审继续,经过讯问和质证阶段的详细分析,法庭辩论阶段的争议焦点已经非常清晰,主要围绕几个核心问题:陈满有无作案动机,有无作案时间,有无异常表现,供述如何形成,在案证据指向,事实是否清楚等。
检方问及陈满狱友的证词和刑讯逼供的证据问题,陈满的情绪再次激动起来。辩论阶段陈满是被审判长要求站着的,他声音大起来,略带委屈的嘶哑:“刑讯逼供,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他们当时这么说了。”检方认为办案机关证明自己没有刑讯的证据确实不具有证明力,是否实施了刑讯逼供是存疑的。易延友也对公安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提出质疑:“我认为这个《情况说明》要一分为二。关于没有刑讯逼供的部分肯定是不真实的。但是办案人员说对陈满很关心,还给他买了面包和水,这个可能是真实的;但是这并不能证明就没有刑讯逼供。相反,这个证言的表明更大可能性是,他们打了陈满,把人打惨了,心生愧疚,所以才买了面包和矿泉水来安慰他。所以,生活上关照的证言不仅不能证明没有刑讯逼供,反而证明实施了刑讯逼供。”易教授这种逆向思维的论证方法获得旁听群众的共鸣,本来严肃的法庭在易教授睿智的质证意见下突然爆发出一阵哄笑。
易延友进一步分析,刑讯逼供中的证明责任是倒置的。根据刑诉法的规定,只要被告方提供了有关刑讯逼供的线索或材料,就应当推定刑讯逼供存在,从而由公诉方将没有刑讯逼供的事实证明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如果没有证明,就应当认定推定事实成立。本案中陈满也提出了清楚的线索,那么有关办案人员就要自己证明没有实施刑讯,如果证明不了,就应当推定刑讯逼供存在。周围的旁听人员似乎若有所思,仿佛第一次听说刑事诉讼中还有这么一个推定。
法庭辩论进行了两轮,辩论的结论高度一致,均认为陈满无罪。审判长提醒大家不要重复,简单扼要地进行辩论,言下之意是要节省时间。比较而言,平心而论,本案合议庭已经在庭审中显示了足够的耐心和高度的公允性。
三、
从个案到制度
(一)最高检无罪抗诉第一案
陈满案被认为是最高检无罪抗诉第一案,充分体现了司法监督的决心和大刀阔斧的勇气;因此吸引了众多媒体的关注和报道。审理结束后众多媒体对易教授进行了采访。易教授认为,最高人民检察院之前也曾经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生效的判决提出过抗诉,但那一直是针对重罪轻判或有罪不判的情形;这一次明显不同,是针对下级法院将无辜的被告人潘伟有罪的情形,最高检认为无罪,而向最高法提出抗诉。另外,最高检以前也曾经纠正过不少冤假错案,但是一直走在幕后,从未采用抗诉的形式,而是采用向法院发检察建议的方式;这一次直接向最高法提出抗诉,表明最高检希望从幕后走向前台,希望在平反冤假错案方面能够有更大的作为,能够让人们也看到最高检的努力。
(二)刑讯逼供是罪魁祸首吗
也许在一边感怀悲悯的同时,更应该冷静地反思,是否身陷于一边平冤一边造冤的制度困境。翻开诸多冤案的卷宗,人们不难发现无一例外地存在刑讯逼供。陈满一提起他所遭遇的刑讯时,情绪就按捺不住地略显激愤,他讲的细节清楚,若不是亲身遭受,怎能描述地如此真切。然而,海口公安机关自己说明没实施刑讯,用以证明的证据却是自己买了水和面包给陈满,这样的证据显然不具有证明力。
细思至此,刑讯逼供是冤案酿成的罪魁祸首吗?也许它不是唯一的原因,但却是最为关键的原因。然而,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如何避免刑讯逼供?如何从源头上最大程度地避免冤案的形成。法律规定其实已经非常清楚和完善了,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为何法律并未被严格遵循,刑讯现象更并未得到足够严肃的重视。
就本案言,陈满身陷囹圄23年之后,仿佛终于等到了迟来的正义。外面世界已经今非昔比的发生了巨变,年迈的双亲还在等待儿子归来。当年他被关押的时候,正是29岁的大好时光,而今他将重获自由,却已鬓发苍苍的52岁。悲哉,被冤入罪的二十三年;喜哉,陈满及其亲友包括诸多默默帮助他的律师们的坚持得到了回应,终于等到最高司法机关还原了案件的真相,最终扳回了正义。这场冤案的平反,即使针对个案而言,也顶多算是一部五味杂陈的悲喜剧。
(三)学者参与辩护实务的亮点
陈满的辩护人易延友最后提到,也许陈满案将获得昭雪,但是真正需要反思的是一个冤案是怎样形成的,最重要的是如何防止刑讯逼供。对此,易教授提出了应当赋予被告人在被讯问时的律师在场权,方能真正杜绝刑讯逼供;同时,应当赋予被告人与提供了不利于己的证言的证人当庭对质的权利,以及申请法庭强制传唤能够提供有利于己的证人出庭作证的权利,进一步防止冤假错案。
我由此想起苏力老师在2015年11月份的一次讲座中提到:“法律人更可能在中国社会成为一个掮客”。具体而言,其认为“法律的职业特点本来就是受雇于人,而且必须忠实于客户,这是它的美德,这种职业特点很可能使法律执业人进入立法时不是从全局出发,不是先天下之忧而忧,法律人更可能在中国社会中变成一个掮客,趋于为重大利益集团所利用。”而针对刑事辩护,苏力老师又专门讲:“刑事辩护律师永远是比控方检察官要容易得多,只要挑你一个刺,挑不出实质性的刺就挑程序性的刺,只要一根刺就行了。我们知道挑刺永远比证明更容易。”(苏力:《社会分层与立法问题》)
我又想起易教授在南昌大学周文斌案中那篇广为人知的辩护词,并不仅仅是对控方证据的简单挑刺,而是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表述及其意义空间作了更加深刻的解读,对毒树之果原理是否包含在我国立法表述中作了精准的阐释,也对“排除合理怀疑”这一证明标准进行了生动的论述。易教授多年来一直倡导对刑事诉讼法进行解释,而不是动辄加以批评。正是坚持这一研究路径,使得他的学术观点往往出人意料,却又更加契合于当下的司法实践;在易教授的著作中,既能够读到精深的法学原理,又能够将其运用于具体的司法案例。也许易教授因有深厚的学者背景,使其能够真正从司法大局出发,从个案延伸到制度反思;他也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律师(尤其是学者型律师)可以不是掮客,而更可能成为司法进步的推动者。
无论是律师界,媒体界,抑或社会各界,我想我们都希望有更多这样的推动者,挑得一手好刺,却不仅仅只是挑刺,而是去治愈法律和良心皆不能承受之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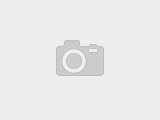 图集
图集 图集
图集 图集
图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