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毛立新
编者按
2019年4月14日,“刑事辩护制度四十年的发展、不足与展望”主题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此次研讨会由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刑事辩护专业委员会与中国政法大学国家法律援助研究院共同主办,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公安部等部门有关领导出席了研讨会。来自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等二十余所知名高校的近60位专家学者和来自全国各地的40余位知名刑事辩护律师参加了研讨会。
北京市尚权律师事务所主任毛立新律师应邀参加了研讨会,并在“刑事辩护制度的完善与展望”单元发表了题为“重视和加强侦查阶段辩护”的主题演讲。以下是整理后的演讲内容,刊发供大家参考。
1979年刑诉法颁布以来,刑诉法历经1996、2012、2018三次修订,总体上看我国刑事辩护制度不断完善,实现了辩护从审判阶段到侦查阶段的覆盖。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刑事诉讼的两头,仍然存在着两个薄弱环节:一是侦查阶段的辩护,二是死刑复核阶段的辩护。尤其是侦查阶段的辩护,目前最为薄弱。
而从应然性和必要性而言,侦查阶段辩护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值得高度重视。主要原因:
一是我国刑事诉讼构造,基本上还是案卷中心主义,实际上是侦查中心主义,侦查结果基本上决定了起诉、审判结论,冤假错案的发生,追根溯源也都是因为侦查阶段出了问题;
二是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和速裁程序的推进,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的诉讼进程加快,审判程序明显简化,当事人诉讼权利有所克减,辩护空间缩小,如果审前程序中的辩护权保障也不充分,案件质量就难免会出问题。
因此,学术界、实务部门和律师界有必要高度重视、进一步完善侦查阶段辩护制度。对此,我有以下建议:
一、将辩护律师介入的时间提前至犯罪嫌疑人到案后、讯问前
1996年刑诉法增加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2012年修订的刑诉法,删除了“第一次讯问后”中的“后”,并明确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身份是“辩护人”。仅从字面看,似乎律师在犯罪嫌疑人到案后、“第一次讯问”前或者过程中就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而不必等到“第一次讯问”结束后。但实际上,不仅讯问前会见犯罪嫌疑人不可能,讯问过程中同样也不可能,实践中都是在第一次讯问结束后,甚至是在结束后很久,才能会见上犯罪嫌疑人。
但恰恰是在到案后、讯问前、讯问中这个时间段,犯罪嫌疑人最需要律师帮助。正是因为此,为解决委托律师、法律援助律师难以及时到位的问题,英国、日本等国家才创设了值班律师制度,由值班律师为到案后的犯罪嫌疑人提供应急性的法律服务。而我国的值班律师,恰恰在这个环节没有发挥出作用,而是把主要职能定位在为“认罪认罚”进行见证上。这是个方向性的偏颇。因为值班律师的功能,应定位于“急诊科大夫”,为到案后的犯罪嫌疑人提供及时法律帮助,而参与“认罪认罚从宽”则应由法律援助律师承担。
到案后的讯问阶段,是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最容易受到侵犯、最需要法律帮助的阶段,也是最容易出现不自愿供述、虚假供述的阶段,必须保障律师及时介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必要的法律帮助。因此,应将辩护律师介入侦查程序的时间,明确为“到案后、第一次讯问前”这个时间段,由犯罪嫌疑人聘请的辩护律师或者值班律师提供法律咨询等服务。
二、切实保障当事人会见辩护律师、获得法律帮助的权利
会见权,既是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更是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会见辩护律师、获得法律帮助,这是被告人的一项基本诉讼权利。会见难,表面看是侵犯了律师的会见权,其实是侵犯了当事人会见律师、获得法律帮助的权利。
目前,我国仍然存在“会见难”问题,主要原因:
一是立法层面,刑诉法规定“危害国家犯罪、恐怖活动犯罪”两类案件会见需要经过侦查机关批准,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对两类案件的范围界定过宽,监察委留置对象目前则完全不允许会见律师;
二是在执法层面,一些地方的看守所和办案单位违法限制律师会见,在“三证”之外增加不必要的手续,对“两类案件”之外的案件也要求办案机关批准,这在涉黑涉恶案件上表现突出;
三是在刑事辩护全覆盖的背景下,律师会见量剧增,一些地方看守所的会见室严重不足,不能满足正常的会见需求。
上面三个方面问题,都需要解决。近来,看守所会见场所不足的问题目前正在逐步解决。但前两个问题仍然比较突出。解决的出路,我认为首先在立法层面,应当明确被留置的对象,同样有权会见律师、获得法律帮助;其次,应该明确违法限制律师会见的法律后果,增加规定程序性制裁措施。考虑到侵犯会见权实际上是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诉讼权利,进而影响到其供述的自愿性,因此,应当规定在此期间获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予以排除。只有这样,才能有效解决违法限制会见的问题。
三、对批捕程序进行诉讼化改造,允许律师阅卷和发表意见
在无罪判决率持续走低的背景下,审前辩护的重要性凸显。同时,在 “捕诉一体”后,捕后不诉的概率降低,捕前辩护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但根据目前的立法和实践状况,审查逮捕阶段的律师介入,面临一些制约因素:
一是侦查机关提请批捕,检察机关受理审查批逮,往往不通知律师,使律师难以及时介入;
二是检察机关审查批捕,目前仍然是行政化的内部审批程序,缺乏三方参与的诉讼构造,律师介入和发表意见均没有平台;
三是律师在侦查阶段对案情的了解十分有限,对报捕案卷没有阅卷权,难以发表有针对性的法律意见。
为解决上述问题,充分发挥审查逮捕程序的审查、过滤功能,充分发挥律师在该程序中的作用,有必要在立法上进行以下改革:
一是明确规定,侦查机关提请批捕,检察机关受理审查批逮案件后,应当立即通知辩护律师;
二是对审查逮捕程序进行诉讼化改造,采用听证的方式,听取侦、辩双方的意见,在此基础上再做出是否逮捕的决定;
三是赋予辩护律师对报捕案卷的阅卷权,以便辩护人更多了解案情和证据,有针对性地发表意见。
另外,在逮捕之后,有必要定期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并允许辩护律师发表意见,在此基础上决定是否延长羁押期限,改变羁押期限跟着办案期间自然顺延的局面。
四、明确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
对于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可否自行调查取证,刑诉法不是很明确,有必要进一步明确规定。
另外,刑诉法目前仅规定辩护律师可以向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申请调取证据材料,没有规定可以申请公安机关调取证据材料,有必要补充规定,以提高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获取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证据材料的能力。
五、强化对查封、冻结、扣押涉案财产措施的司法救济
近年来,中央不断强调对公民尤其是企业家的财产权保护问题,而侦查实践中查封、冻结、扣押等措施的适用长期以来存在混乱,亟需解决。
解决的路径:
一是可以考虑强化司法救济,对侦查机关违法采取查封、冻结、扣押措施的,当事人及其辩护人不仅可以向检察机关申诉、控告,还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二是可以考虑将查封、冻结、扣押等强制性侦查措施的决定权,逐步由公安机关移交给检察机关。
六、保障辩护律师对程序性事项的的知情权
侦查机关在变更强制措施、变更羁押地点、向检察机关报捕、移送审查起诉时,均应当及时通知辩护律师,保障律师对这些程序性事项的知情权。
为此,建议在侦查程序中增加规定,上述程序性诉讼文书在送达当事人的同时,还应当立即送达给或者通知到辩护律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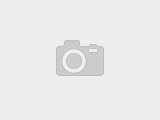 图集
图集 图集
图集 图集
图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