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4年5月,北京市尚权律师事务所与中国政法大学刑事法律研究中心共同创办了“蒙冤者援助计划”项目,旨在为蒙冤者洗清罪名,促使司法机关纠正重大冤假错案。“蒙冤者援助计划”即是借鉴并学习了美国的“无辜者拯救项目”。
“无辜者拯救项目”是1992年纽约州叶史瓦大学“本杰明•卡多佐法学院”的贝瑞•谢克和彼得•纽弗德共同创建的。自启动以来在这个项目所受理的求助申请中,有43%最后证明求助者无罪。
2008年7月3日,美国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帕特里克·沃勒(中)在法庭上被宣告无罪时,当场高举双手欢呼。1992底,沃勒被控绑架等罪名入狱16年,在洗冤工程中,基于DNA的鉴定终获无罪。
自由迟来的公义

2005年12月15日,当埃尔金斯终于以一个自由人的身份走出美国俄亥俄州的曼斯菲尔德监狱,他因为一起涉及重度谋杀、强奸及加重性侵犯的错误定罪被判终身监禁,并已服刑8年。
一年多前,俄州“洗冤工程”受理了埃尔金斯的申诉,并通过DNA检测证明他并非凶手。
然而,启动案件重审的道路上满是荆棘坎坷,直到埃尔金斯和洗冤工程意外找到真凶才让事情重现转机。在连续不断的失望过后,突然间的沉冤昭雪让埃尔金斯有些措手不及。当他终于重获自由时,他最关心是让妻子和孩子们在那个风雪交加的日子里小心驾驶。
“对于这些获释的人,你会为他们的平静深深震动。”俄州洗冤工程负责人、辛辛那提大学法学院教授马克·戈德森,是埃尔金斯案的直接参与者。
2013年10月6日,戈德森在北京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他说,“在愤怒中度过余生将是一场悲剧,蒙冤者必须学会控制情绪、克制愤怒。”确如戈德森所言,虽然往事不堪回首,埃尔金斯仍淡然处之。“在经历过错判和冤狱之后,他们几乎可以克服任何事。他们对自由怀有深深的敬意。”戈德森说。
冰山一角原来美国冤案也这么多

2011年10月21日,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市安哥拉镇,在教养所的洗冤工程办公室里,亨利·詹姆斯正在愉快地享用平冤后的第一顿“大餐”。在此之前,詹姆斯因被控强奸罪已经服刑将近30年。
事实上,埃尔金斯只是美国众多蒙冤者中的一员。
截至目前,全美各州的洗冤工程(INNOCENCE PROJECT)已通过DNA技术帮助311名被错判的蒙冤者重获新生,其中18人获释前正在等待死刑的到来。
2011年10月的一天,当近百位获释的冤案受害者在洗冤工程的一次会议上集体站到聚光灯下时,所有与会者都受到了震撼。
“对于美国的司法系统,人们总是怀有某种迷信,而最大的迷信就是我们从来不会犯错。”美国俄亥俄州前检察总长吉姆·佩特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尽管洗冤工程已让数百人成功获释,“但与监狱里那些依然无法洗脱罪行的蒙冤者相比,这只是冰山一角”。
2005年,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学院的一支研究团队根据公开报道,对本国1989至2003年的冤案进行了统计。结果表明,22%成功洗冤的犯人来自于死刑案件,而死刑案件在所有既决案件中的比例只有0.1%。
凭着犯人们口口相传,戈德森所在的俄州洗冤工程在10年间收到了6000多封狱中来信。在辛辛那提大学法学院罗森塔尔司法研究所的办公室里,3名专职律师和20名法学院学生认真阅读每一封来信,并为来信者寄回一份长达23页、包含了几百个问题的调查问卷,以详细了解案件发生和处理中的每一个细节。
“其实有些犯人并不了解洗冤工程是干什么的。他们会说,‘我是犯了罪,但判我20年太重了,15年就行了’。还有些人,你一看就知道他在撒谎,只不过是想出狱。”戈德森说,对于那些自称无辜又能取得洗冤工程信任的人,团队成员们会展开调查。
首先,洗冤工程需要判断案件发生过程中是否可能留下DNA样本。
“如果有个人走进来给我一枪然后迅速离开,他是不会留下DNA的。”戈德森解释,“这样的案子我们基本不能受理。没有DNA,我们能做的事情非常有限。”
依据俄州经验,90% 的案件中不可能存在DNA样本,所以真正进入调查程序的案件只有大约10%。
这10%的案件大多数涉及强奸和伴有打斗的谋杀,因为凶手常在强奸现场留下精液,或在受害人的指甲中留下皮肤组织。洗冤工程也常常利用这两点进行洗冤。
正如佩特罗在《冤案何以发生》一书中提到的,运用DNA技术缉凶未必100%准确,但将它反之应用到洗冤中“进行否定排除”时,则能起到100%的确定效果。
不过,想在几十年前的案件中寻找DNA证据绝非易事。除了不停探监向当事人了解情况,团队成员还要通过电话寻找并登门拜访当年办案的警察、法医和辩护律师等。他们要不断向当局乞求,才能获准接触到当年的物证。而每一个步骤执行起来,均可谓步履维艰。
令人沮丧的是,不懈努力换来的往往只有失望。在超过75%的案件中,那些陈年旧证早已遗失或损毁,想在检测后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无异于痴人说梦。
戈德森喜欢用“足够幸运”形容那些能够找到DNA证据的案件当事人,但幸运并不代表无辜。
经过DNA检测,50% 的当事人被证明正是凶手,25%的案件无法得出确定性结论,剩下的25%可能成功洗冤。
“这就像一条拥挤的公路,每前进一段就会出现几条岔路分流走大部分车辆,走到公路尽头时,车辆已是历历可数”。
戈德森说,俄州洗冤工程开展10年至今,只有约30人一路前行直到向法院申请重审案件,比例约为0.5 %。
“但是这并不表示剩下的99.5%的人有罪。只能说很多人不够幸运,找不到可以检测的DNA。”戈德森说。
阻力难以承受的洗冤成本

媒体的压力是检察官得以低头的一个重要因素
然而,向法庭申请重审案件远非这条路的尽头。在俄州洗冤工程约30名申请重审的当事人中,最终沉冤得雪的只有17人。
“从现在的情形看,洗冤工程遇到的最大障碍就是检察官和法官不愿承认自己犯错。即使普通人看过案件报道后都认为这个人是冤枉的,到了检察官和法官那儿,他们还是会说‘不不不,这个人有罪’。”戈德森说,即使在美国,洗冤工程在办案中同样阻力重重。
从寻找证据进行DNA检测开始,司法人员便可利用职务便利和自由裁量权对洗冤施加干预。
2004年,被判犯有强奸罪、故意伤害罪、绑架罪的雷蒙·托勒被获准对物证进行DNA检测。然而,在执法人员的两次阻挠和一次无效鉴定后,直到2010年托勒才真正收到最终的检测结果。从错误判刑到最终获释,托勒在监狱中蹉跎了29年的光阴,而为了获取公正的DNA结果,他足足等了6年。
对于很多蒙冤者来说,托勒在DNA检测后无罪出狱令人艳羡,因为他们很多人并没有那么幸运。
依据美国法律,如果被告在宣判后发现可以改变原判的新证据,可提交动议申请重审。
但现实中,法官对新证据的要求十分严苛,常常超过法律规定本身。很多由洗冤工程代理的案件都获得了强有力的新证,却无法启动重审,原因正在于此。而案件即使重审,是否重新公诉的决定权仍掌握在检察官手中。
俄州洗冤工程正在代理的一起案件中,当事人被控抢劫一家商店并用塑料绳捆住了女店员的手脚。从店员手腕、脚踝处的塑料绳上,团队成员发现了同一个人的DNA 样本,但显然并不属于他们的当事人。
此外,虽然监控录像无法体现劫犯的面部特征,科学家们却通过比照门窗高度测算出劫犯的身高。“录像上的男人只有5英尺10英寸(约1.78米),而我们的当事人很高,足有6英尺4英寸(约1.93米)。这个差距相当明显”,戈德森说。
然而,即便手握关键证据,洗冤工程在案件重审后仍然连输两局,“他很有可能要继续坐牢。原因很简单,检察官、法官都不愿认错。”
客观公正地看待自己犯下的错误并坦然承认,对于任何人都非易事。
在剖析司法人员拒绝认错的微妙心态时,曾担任美国联邦检察官的戈德森说得很直白:这些人不是坏人,不愿认错是人的天性。“这种心理博弈的过程其实非常有趣。
当人们在一个事情上投入了巨大的时间和精力后,很难再按照完全客观的标准进行判断。
很多时候他们真的认为这个人有罪,但在新证据面前就是脑子转不过弯儿来”,戈德森说,“当然,在美国的司法体制下,很多检察官想当法官或者政客,如果办了错案,无疑会影响他们的政治前途。”
此外,多年冤狱往往意味着巨额赔偿。根据俄州法律,埃尔金斯出狱后,可以获得包括因监禁损失的工资、律师费等在内的共28万余美金的赔偿。
此后,他又以俄州萨米特县检察官办公室、县政府和巴伯顿市警察局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仅巴伯顿市就要因此承担540万美金的民事赔偿责任,因为侦查、起诉过程中执法人员哄骗6岁的受害人做出了不利于埃尔金斯的证言,而这份证言并不准确。“巴伯顿市为这场诉讼付出了巨大代价,对于那样一座小城,540万实在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大概相当于纳税人一年的税款。”佩特罗的妻子南希说到,“不过这或许可以改变警察的做事方式,因为肯定有人告诫他们永远别再捅出这么大的娄子。”
然而,那些抗拒洗冤的司法人员或许忽略了一个事实——正如俄州公设辩护人蒂姆·杨所说:在全州范围内,检察官用于对抗犯人获得DNA检测的时间和金钱远远高于检测成本本身。
而佩特罗也在《冤案何以发生》中算过一笔账:在迈克尔·格林案中,如果进行了DNA检测,俄州及克利夫兰市将省去赔偿冤狱损失的260万美元,以及约25万美元的监禁成本。
薪火相传那些为洗冤工程付出心血的人们

左边:《你好,真相!》一书收录了美国的48例冤案。截至2013年10月中旬,美国的洗冤工程,已经成功为311名蒙冤者洗清罪名。
右图:美国俄亥俄州前检察总长吉姆·佩特罗在《冤案何以发生》中认为,运用DNA技术在洗冤中能起很好的效果。
“百夫长事工”
1980年代,美国一位名为詹姆斯•麦克罗斯奇的退伍军人在攻读神学硕士同时,于一所监狱中兼任见习牧师。为狱中结识的一名蒙冤犯人所触动,1983年麦克罗斯奇获得学位后与志同道合者一起成立了非赢利性组织“百夫长事工”(Centurion Ministries)。
“百夫长事工”致力于帮助那些声称自己无罪的被告人或监狱囚犯重检证据与审判经过,发掘其中真正能洗脱罪名、免除牢狱之灾的蒙冤者,进而彻底消除无辜者被判有罪的现象。
而麦克罗斯奇在狱中结识的蒙冤者桑托斯,就是由“百夫长事工”澄清罪名获得改判的第一人。
“百夫长事工”是之后风行全美的“无辜者拯救项目”的第一个先行者。
“无辜者拯救项目”
二人在经过对 18000 例刑事案件的鉴定后,发现有相当数量的刑事案件鉴定、采信证据的程序不适当,这就意味着其中相当多的人很可能是被错判的。
因此两人发起了一项由法学院教授和管理人员监督的法律实践项目,以向那些声称自己无辜的监狱囚犯提供司法鉴定协助为宗旨。
在这个纽约的“无辜者拯救项目”受理的所有求助申请中,有43%最后证明求助者无罪。
直至今日,此类“无辜者拯救项目”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在美国各地成立,以至于有人把“无辜者拯救项目”的蓬勃发展过程称为“新民权运动”。
在美国,洗冤工程是一个有着长期组织与行动传统的法律人网络。
这些来自社会的力量不仅使蒙冤者获释,还试图推动立法,以补救美国法治系统的种种漏洞。
傲慢与改变

如今,美国大部分州都有类似组织,这些通过DNA技术挽回个案正义的法律援助项目,已对司法实践乃至美国法律体系带来变革。
在戈德森看来,人们对狱中伸冤者的无视、对法庭判决的盲目信赖,恰恰显示了司法系统的傲慢与自大。
而与个案公正相比,让人们认识到司法弊端和人类认知的局限性并在今后的调查、公诉、审判中谨慎行事,意义似乎更加深远。
2003年戈德森创建俄州洗冤工程时,便到州议会讲解冤案问题,并商谈改革刑事司法程序中的细节。
十年后,戈德森依然无法忘记当时议员们的反应,“他们看我的那种眼神,好像我是个疯子”。
在南希·佩特罗看来,改变就像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尤其是对公共政策的改变。“我们只有一点点争取,一个州一个州地逐一争取。”
此后的每一年,戈德森都会带着相同的问题来到州议会并提交报告。
6年后,议员们终于开始认真考虑戈德森的建议。“大概说了这么多年,他们渐渐适应了”,戈德森笑着说。
经过洗冤工程和佩特罗等人的游说和多番激辩,2010年俄州终于通过了证据保存法,其中规定所有刑事证据必须保存至被告出狱。与此同时,规范统一的目击证人指认程序也逐步建立。
如今,在目击证人指认嫌犯时,执法人员不能进行任何暗示,且须逐一出示每一位嫌犯照片,同时,参与指认程序的执法人员不得了解警方的调查方向。
此外,以得克萨斯州为首的一些检察官建立了“完整定罪联盟”。通过官方与民间的合作,检察官们让一些顶尖级的律师复查那些自己可能办错的案件。如果一个正在服刑的犯人因为坚持不认罪而多次拒绝、丧失假释的机会,他的案件就可能得到联盟的复查。
“我们所做的不仅是纠错,而且是创造”,南希·佩特罗说,“当问题被发现、被正视之后,人们就会想法设法加以解决。”
就在越来越多的蒙冤者重获自由时,一些司法人员也在沸腾的民怨中受到惩罚。
得克萨斯州的迈克尔·摩根案中,先后两任检察官均对被告隐匿了能够证明其无罪的DNA证据,摩根为此坐牢25年。经媒体多方报道后,摩根案引发了全国性的影响。经手案件的前任检察官,其时已是一名法官,尽管享有绝对的起诉豁免权,却不得不在法官任上尴尬辞职。而那名8年来不断阻挠DNA检测的继任检察官,虽然德高望重,也在之后的选举中大幅落败。
“是美国人民在推动改革,迫使检察官们去做那些正确的选择”,南希·佩特罗说。
当人民逐渐醒悟到司法体系的缺陷时,那些从俄州、得州或其他地方发起的点滴努力,也逐渐在整个美国遍地开花。
目前,戈德森正在推动一项旨在提高指纹鉴定专家独立性、规范指纹鉴定程序的法案。尽管法案尚未通过,但戈德森对此给予厚望。他一遍又一遍重复着那句话:改变需要时间,或许要持续几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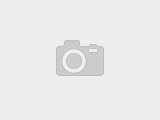 图集
图集 图集
图集 图集
图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