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正案九》第三十六条要赶走、吓跑多少辩护律师们!
原标题:韩嘉毅:坚决反对刑法修正案九之三十五条
关于《修正案九》第二稿第三十六条(第一稿第三十五条)
旧文重发。
作者:
韩嘉毅,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业务委员会秘书长
来源:京都律师事务所

1_150625153255_1
《刑法》规定了什么是犯罪行为、以及如何惩治,是最严厉的、最残酷的法律,当其他法律不足以保护正当社会关系时,才能启动的最后法律防线。刑法的修订不仅关系到每一个公民的行为尺度和界限,还体现出立法者运用刑法的态度和智慧。正在征求意见的刑法修正案(九),之所以备受法律人,尤其是律师的热议,因为它设定了有可能是针对辩护律师、针对辩护律师执业行为的犯罪条款。
罪责相适应、罪刑法定,这是刑法立法的基本原则。律师的执业行为有没有必要上升到运用刑法加以惩治,目前的立法草案一旦成为法律能不能被扩大解读,这是所有律师关注的问题。从目前公布的修法草案看,律师的担心不无道理。
刑法修改草案第三十五条规定:
将刑法第三百零九条修改为:“有下列情形之一,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
“(一)聚众哄闹、冲击法庭的;
“(二)殴打司法工作人员或者诉讼参与人的;
“(三)侮辱、诽谤、威胁司法工作人员或者诉讼参与人,不听法庭制止的;
“(四)有其他严重扰乱法庭秩序行为的。”
(注:第三、四款是新增条款)
修改刑法309条,增加规定第三、四款,将刑罚扩大到“不听法庭制止”和“其他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行为”的理由不充分。司法实践中,涉及刑法309条所指的案件是否呈现爆发的趋势?通过“侮辱、诽谤、威胁”和其他行为扰乱法庭秩序的现象是不是大量存在?导致审判秩序处于混乱状态的案件是不是大量发生?游走于各级法院的律师们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纵观三大诉讼法的规定,法律已经赋予法庭多种司法惩治权,从三十年的司法实践情况来看,人们已经习惯于尊重法庭的权威,可以说,法律赋予法庭的司法权力足可以实现维持法庭秩序的目的。既然没有大量的案件发生,法律赋予法庭的权利也能保证法庭权威,还要进一步通过修订刑法来加强法庭的控制力,原因只能是因为极其个别的案件发生,被立法者认为不仅是严重挑战了法庭权威,而且影响极坏、备受关注,有越演越烈的趋势。这让我们不得不想到近期来被广为诟病的“辩审冲突”,这应该就是修法的理由。
从法条表面字义来看,设定此罪名的意义在于保护司法工作人员和诉讼参与人,因为他们可能成为该行为的侵害对象,律师也在被保护之列,应该甚是欢喜才对。但结合目前司法实践的情况来看,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随着法治理念的深入人心,随着律师队伍的越发成熟,委托人和他们的律师们越来越不满足流于形式的庭审。而这种追求庭审有效性的诉求进步,必然与法庭懒惰的惯性运行产生难以弥合的激烈冲突。在这种对抗中,能够、敢于不听法庭指挥、命令的,常常是只有律师。因为懂法、因为确信有人违法、因为确信自己是在守法、也因为相信法律的保护,所以律师才敢持法律以挑战法庭权威。我想正是因为律师在法庭上的一次次不听命令,才使个案被社会广为关注,才引发这样的立法想法。其实,加强对律师的控制,从严治理所谓的庭审乱象的想法由来已久。随着刑诉法的实施,最高人民法院在制定司法解释的草案中,也在第二百五十条中规定了针对律师的强制手段。只不过由于司法强权的态度过分暴露,引来阵阵强烈的声讨和反对之声,才不得不就此罢手。但面对越发强烈的对流于形式的庭审冲击,修法是重新制定规则、立好规矩的大好时机,有充分话语权者不可能袖手旁观,于是就有了这看起来是保护,实为惩治的条款。
春暖鸭先知!此条修法影响之深远,只有从事律师职业的人,才能深刻感受其散发出的刺骨寒冷。这也正是为什么那些不做刑事辩护的律师们,北京的刘红宇律师、上海的胡光律师,纷纷以政协委员的身份发出反对声音的原因!
笔者认为,坚持审判中心原则、坚持独立审判原则,是法治建设的正确道路。但前提是坚持法律至上的原则,而不是法官至上的原则。只有遵循法律至上,才是维护法庭秩序的根本途径。狭隘的扩大审判权、没有限制地遵循法官至上,试图通过加大打压的力度来实现法庭上的和谐审判,不仅仅是犯了头痛医脚的错误,更是后患无穷的倒退做法。因势利导顺应这种追求庭审有效性的诉求,将使我们的法治建设迈出坚实的一步,相反,司法强权的错误观念如不能得以纠正,也将会更加严重地阻碍法治进程。
从立法技术的角度上看,此种修法也不能符合法治精神。刑法谦抑性要求刑法的处罚范围要收缩、抑制和内敛,尽可能减少刑法适用,体现“慎刑”思想,不能滥用刑罚。控制刑法介入社会生活的广度和强度,避免因刑法的过度适用导致对公民权利的侵犯。刑法确定性则要求法律规定必须清晰、明确,没有主观擅断空间,可以被任何人用来预测行为结果是否应当受到刑罚处罚。这是刑事立法的基本原则。所谓“其他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行为”与这样的原则显然是背道而驰的。再看侮辱、诽谤行为,刑法246条已经对侮辱诽谤规定了罪名。侮辱、诽谤行为必须达到情节严重时,告诉才处理,就是因为侮辱、诽谤行为的后果,一般情况下可以用包括民事法律关系在内的其他法律关系调整,不足以运用刑法手段加以规定,体现的正是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当然,刑法246条也规定了无需告诉直接追诉的例外,就是对于涉及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情况。如果在法庭上的侮辱、诽谤可以被直接适用刑罚处罚,就意味着在法庭上的侮辱、诽谤行为的危害,等同于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这是不能让人接受的。至于法庭上的“威胁”可以入罪,更是令人不解。公堂对簿,必然唇枪舌剑,语言上威胁在所难免,就算随时制止、也会随时再犯。如何认定威胁、威胁的性质,主观擅断的空间很大。这与刑法的基本原则也是相违背的。
法庭权力过大,加之立法上的模糊表述,只会进一步挤压辩护空间,不利于法庭兼听则明,最终影响的是我们实现保障人权、依法治国的根本目标。司法实践中,控辩双方在庭审中地位悬殊,此种情况并没有随着新《刑诉法》的实施有任何改变的迹象;本该保持中立、居中裁判的法官,却常常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在法庭上压制被告人、律师,导致律师不能充分发表意见,甚至出现大量审辩冲突的怪现象,这也是不争的现实。控、审两方权利过大、行使权利缺少监督和制约,让辩护律师没有职业尊严、没有执业安全,使大量律师远离刑事审判法庭,在这种情况下,再将主观性很强、可以产生不同理解的“侮辱、诽谤、威胁”、“不听法庭制止的”,以及可以扩大解读的“其他严重扰乱法庭秩序行为”,在没有前置处罚、没有程序设计和救济的情况下,直接规定为犯罪行为,必然导致的结果可能就是司法权的进一步滥用,辩护空间被进一步压缩。
国家之所以设立律师制度、建立律师队伍,其目的就是站在被追诉的嫌疑人、被告人一方,与公权力的运行进行对抗,避免国家权力的滥用。辩护律师注定就是一支任何法治国家、法治社会都需要的,为了与公权力的对抗而生的队伍,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和生命就是对抗国家强权。为此,诉讼法中除规定了辩护制度外,还规定了控方举证、不得自证其罪、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等等扩大被追诉方对抗权力、限制追诉方追诉权力的规定,同时,各个国家对于律师执业的规定,包括联合国的《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等,都特别制定了律师执业的豁免权,才能让原本就不可能公平的对抗,在法律的特别保护下,变得尽可能公平。制定刑法也要符合限制国家权力滥用的精神,这才是符合法治的精神。
在我们的司法实践中,辩护权的充分行使是不是已经导致了放纵犯罪?如果是这样,那么就确有必要压缩辩护空间,不放纵犯罪。如果相反,我们保护人权不力,侵犯人权、甚至产生了冤案、错案的情况时时发生,辩护律师的作用就没有充分发挥,就应该积极鼓励律师充分发挥作用。我们刚刚将保障人权写进刑诉法,公众对于法治的现状和期许还存在较大差距,显然我们并不属于前者。我们公认的刑事案件辩护率不足30%,许多律师谈刑辩而色变,这与我们太差的法治环境有直接的关系。这样的刑法修法,会让多少律师更加远离刑事法庭、也让多少走进刑事法庭的律师,不敢对抗强权。实际受损的不仅仅是个案中被告人的利益,最终影响的是法治建设、依法治国的战略目标。
看不懂的修法,它能让辩护人轻易地就变成被告人!将要赶走、吓跑多少辩护律师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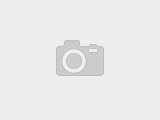 图集
图集 图集
图集 图集
图集




























